李格悌
戰火餘生
李格悌生活在不同文化、語言、民族和宗教的交會處:「我出生在特蘭西瓦尼亞,是羅馬尼亞國民。然而,我從小就不會說羅馬尼亞語,我的父母也不是特蘭西瓦尼亞人。 我的母語是匈牙利語,但我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因為我是猶太人。但是,我不是猶太社群的成員,而是被同化的猶太人。然而,我也沒有完全被同化,因為我沒有受洗。 » 1929 年,李格悌全家搬到了該地區的首府克盧日(德語為克勞森堡,匈牙利語為科洛斯瓦爾),李格悌在那裡學習了羅馬尼亞語。身為匈牙利人和猶太人,他從 1933 年起就面臨許多問題:尤其是 1941 年他想修讀物理課程的大學被拒絕。 1944 年,猶太人必須佩戴黃星標誌,並成為大規模驅逐的受害者(作曲家的父親和兄弟死在集中營中)。李格悌被編入匈牙利軍隊強制勞動隊進行強制勞動,兩度逃脫死亡。隨後他返回的家庭公寓被陌生人佔據。在那裡,他會找到他的母親,她是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的倖存者。戰後離開克盧日,李格悌在布達佩斯的弗朗茨·李斯特學院開始了更高的音樂學習,他的老師是桑多爾·韋雷斯、帕爾·賈德拉尼和費倫茨·法卡斯 (Sándor Veress, Pál Jádrányi et Ferenc Farkas)。
他對音樂的學習也經歷了同樣的滄桑:他是個早熟的孩子,從小就在內心聽到音樂,但他的父親卻想讓他從事科學事業。十四歲的時候,他想像哥哥一樣學習小提琴,於是得以學習鋼琴。他立即為自己的樂器創作了樂曲,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潛心閱讀了一本有關管弦樂編曲的論文,開始創作一部弦樂四重奏和一部交響曲。然而,對和聲與對位法的深入研究只有在戰爭結束後的1945 年至1949 年間在布達佩斯學院才有可能進行。為標誌。在 Zoltán Kodály 的支持下,Ligeti 於 1949 年開始教授寫作。他寫了兩本和聲專著,後來成為參考書。在柯達伊的敦促下,他運用自己的雙語能力,開始在特蘭西瓦尼亞進行民族音樂學工作。他寫了許多作品,其中一些受到民間傳說的啟發,有些則更加個人化,他隨身攜帶。如果說戰爭結束後的那段時期仍然相對自由的話,那麼從1948 年起,斯大林主義就殘酷地降臨到了匈牙利:巴托克最大膽的作品被禁止,就像所有現代音樂一樣,西方廣播受到干擾,與西方的貿易幾乎不可能。 1956年革命後,受到蘇聯軍隊的鎮壓,Ligeti與妻子秘密逃往奧地利避難。他將立即前往科隆與斯托克豪森和艾默特一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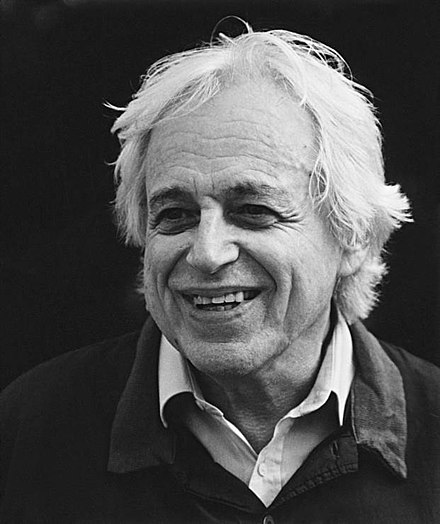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飽受折磨的傳記因為它構成了作曲家美學選擇的基礎(儘管部分是秘密的)。在他的音樂中,悲劇的維度實際上會被諷刺和幽默的特徵所掩蓋,而總是以建築作品為媒介的表現力被推向了極致。他的音樂擺脫了直接的悲傷和封閉的系統,旨在打破傳統,玩弄矛盾。Ligeti將這種批判性的、自願挑釁的精神運用在自己身上:每件作品都對前一件作品提出質疑,並探索新的可能性和類別。他對這個主題的可悲的表現的不信任,可以被描述為反浪漫的,是基於經驗的。與保羅·策蘭一樣,被歷史傷痕累累的主觀表達在音樂語言中被重新組合,這種語言從來都不是一種“再現形式”,但在這種語言中,效仿他的朋友、詩人桑多爾·韋厄雷斯(Sándor Weöres)的例子,內容是由形式吸收和產生的。這種方法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件“作品”,它在希爾弗瑟姆頒發官方獎項時被認為是真正的挑釁:《一百個節拍器的交響詩》(1962)。這個標題本身就已經帶有多重意義,還帶有諷刺意味。在經歷了混亂的開始和不同的節奏結構(很大程度上是隨機的)的疊加之後,不可避免地導致節拍器運動滅絕的過程是物體的漸進個性化,它逆轉了個體轉化為物體的過程;它具有真正的表現力,甚至可以說是悲劇性的,就像一股死亡的氣息,無情地到達數百個節拍器中的每一個,直到最後一個節拍器的最後嘎嘎聲。然而,Ligeti對這種毀滅過程的隱含意義隻字不提,這比任何悲慘的音樂都更有說服力。
在李格悌的創作中,三個時期的劃分是不言而喻的:匈牙利時期直到1956年,實驗和微調音樂時期直到1970年代,最後是風格融合的成熟時期。

從東到西
匈牙利時期本身可分為三個時期:1938年至1945年間創作的作品(整體知之甚少,無法做出判斷);直到1950年為止創作的作品,以戰後氣氛為標誌,在戰勝納粹主義之後,作曲家可以相信社會主義烏托邦;最後是「史達林的超現實社會主義」建立後直到1956年他流亡為止創作的作品。後來佔據了主導地位。面向大眾且能夠透過審查的作品與秘密創作的作品(作曲家自己所說的「為抽屜」而作)之間的矛盾貫穿了第一個時期。 1951 年至 1953 年間創作的鋼琴集《Musica Ricercata》在這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這部作品是一系列短篇作品,典型地混合了嚴肅性和漫畫性,在減少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創作,這些材料在作品中擴展,最終在倒數第二首作品的賦格曲中使用了十二個聲音。不久之後,即1953 年至1954 年創作的第一弦樂四重奏《夜間變形》,其副標題同樣具有啟發性,無疑是第一個時期的頂峰:巴托克的遺產以單曲的形式被推向了極致。
接下來的作品《為管弦樂團而作的維西歐克》(Vísiók for Orchestra,1956)代表了李格悌只有在流亡後才能邁出的決定性一步,當時他已經熟悉了西方現代性的各種作品:由史特拉汶斯基所創作的維也納學派的歷史作品。我們如何把握這個改變呢?李格悌在他的第一個時期發展了一種基於半音「調性」的寫作類型,其中音程圍繞著一個中心組織,確保與民間傳說相關的某些調式結構或某些旋律輪廓的整合,以及動機-允許建構形式的主題工作。然而,從1950年代初開始,利蓋蒂試圖擺脫這種思想形式和巴托克風格的影響。這就是他想像的移動結構,其中間隔被中和,主題元素被消除,時間進程僅以靜態形式出現,作為空間中的運動。該材料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題和和聲,而是基於以其內部結構(ambitus、tessitura、參考音階、動態、音色)為特徵的集群,根據蒙太奇原理正式工作:時刻之間的聯繫具有聯想性而非演繹性,包括截然不同甚至矛盾的表達類型;在《幻影》(1958-1959)或《氣氛》(1961)等作品中,它們也與視覺圖像和聯覺效果聯繫在一起。這兩部作品標誌著作者風格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有程序的音樂,沒有程序」。這些“靜態的聚合體,沒有旋律,沒有節奏,按照幾何比例構建”,靈感來自克利或米羅等畫作,部分來自 1957-1958 年在科隆進行的電聲實驗(特別是 Artikulationen)李格悌定居於此,部分原因是他對近代音樂的批判性接受(布列茲的《結構Ia》、施托克豪森的《Gruppen》以及韋伯恩)。
就在這些奠定了他的國際聲譽的第一部作品之後,李格悌轉向了更具諷刺意味的形式,與正在發生的事情相關,例如《音樂的未來》、《鋼琴家的三件小事》 (對4'33 的約翰凱吉的幽默回應)或《片段》為室內樂團而作,嘲笑他自己的幻影——1961年進行的三項實驗。的音樂劇作品,為三名歌手和七名樂器演奏家創作的《歷險記》,其特點是基於手勢的變化和經常突然的不連續性,以及一系列富有表現力的原型。對他來說,這是“直接翻譯人類的情感和行為”,不經過文本的中介,而是使用純粹的語音元素。 「諷刺」、「悲傷」、「幽默」、「色情」和「恐懼」等表達類別構成了形式,分為九個部分。因此,《歷險記》的嘲諷和《安魂曲》(1963 年至1965 年為大量觀眾創作)的戲劇性緊密相連,貝恩德·阿洛伊斯·齊默爾曼(Bernd Alois Zimmermann) 創作的《年輕詩人安魂曲》和《音樂》就是如此。

以前的管弦樂作品中明顯無形的聲音組合讓位於,從《安魂曲》,到由對位法控制的線條交錯,並使用基本的多音律,他自己稱之為“微復調”,然後更喜歡這個術語“超飽和複調”。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埋藏在紋理中的連奏旋律形式。它們將在後續作品中浮出水面。我們也注意到圍繞軸的色彩原理的發展。李格悌遵循了巴托克的教訓:他並不是從可以推導出奇異形式的廣義半音開始,而是將半音視為諧波空間被加法過程填充的時刻(這將很快引導他走向微音程,並產生分支)兩組弦樂器按四分音調音,然後是接下來十年的各種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旋律主題寫作和和聲思維這兩種情況下,李格悌都拒絕達姆施塔特序列主義意義上的任何絕對化:旋律結構是隱藏的、不可識別的,但卻是存在的;全音階與半音階之間、音程或和弦與簇之間的對立得以保留。利蓋蒂反對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包括美學領域內的意識形態。
模糊的、統計上可理解的形式與清晰的、精確確定的形式之間的互補性對於 1969-1970 年間十三件樂器的 Kammerkonzert 或 Melodien (1971) 具有重要意義。她發現自己處於一首具有令人回味的標題《時鐘與雲》的作品中,為十二位女聲和小型管弦樂隊而作(1972-1973),其靈感來自卡爾·波普爾的一項科學研究,其中利蓋蒂試圖掌握「複雜週期」的中間狀態。這部作品與舊金山複調樂團(1973-1974)合作,構成了李格悌第二個創作時期的巔峰。在所有這些作品中,利蓋蒂喜歡根據其內部過程自行轉變和展開的音樂形式。確定性邏輯被啟發、斷裂和不可預測的願景的形式所取代。這使得李格悌更接近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運動,甚至激浪派。這也賦予了他的音樂一種特殊的光環:某些簡單思想的幾乎系統化的發展,以過程的形式,在其自身的邏輯和詩意幹預的作用下被打破。在他高度複雜的作品中,總是存在著一種原始的、基本的元素,它形成鮮明對比,表面上拒絕進入作品明顯的「系統」。

民俗重塑
李格悌的第三個時期是在 1974 年至 1977 年間根據米歇爾·德·格爾德羅德 (Michel de Ghelderode) 的文本創作的歌劇《大恐怖》(Le Grand Macabre) 中宣告的。布勒蓋爾和博斯的世界在作曲家的童年中如此重要,現在強勢回歸(故事發生在布勒蓋蘭)。這也是狂歡節、鬧劇或不敬的流行戲劇的內容。這部作品由一幅巨大的拼貼畫組成,充滿了或多或少扭曲的、或多或少可辨認的引語,從開場的號角開始,讓人想起蒙特威爾第的《奧菲歐》開頭的小號,結束於變奏主題的長篇闡述貝多芬的英雄史詩。李格悌會說他「將音樂史上突出的一切都融入了歌劇中」。過去的元素似乎是用過的、掉落的材料、發現的物體,從中建構了一種折衷的、不純粹的語言。利蓋蒂談到了「黑色、惡魔般的作品,極其陌生、野蠻、殘暴」。這部歌劇不僅要反心理、反敘事,用怪誕、粗俗、下流、粗俗和荒唐的言論取代理想化的情境(我們在其中找到了《歷險記》和《新歷險記》的語音元素,《大驚悚》就是在其中出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歌劇直接來自斯特拉文斯基,經過卡格爾式的解構和馬代爾納(Satyricon)的幽默。如果權力具有怪誕的特徵,那麼即使在假聲男高音王子高高的聲音塑造中,也沒有一個角色能提供絲毫的進化,世界末日只能是偶然避免的。音樂的多元視角主義,累積了層層扭曲的參照,就好像作曲家讓自己由歷史來創作,而不是以真正個人的方式進行創作,指的是視角的完全缺失。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利蓋蒂所有音樂的一個基本特徵,這可以用矛盾的方式來解釋,即拒絕賦予音樂一種同質和統一的形式,或者作為一種超越所有維度的無限感覺(斯坦利·庫伯力克顯然是這樣的)。
當時的評論家並沒有清楚地看到圓號三重奏(1982)在多大程度上擴展了這樣的計劃,這些計劃已經包含在《紀念碑》、《自我肖像》、《為兩架鋼琴而作》(1976)等作品中,甚至包括為羽管鍵琴而作的《匈牙利搖滾》和《帕薩卡利亞非赫雷塞》( 1978)。李格悌在一首由四個樂章組成的室內樂作品中,透過布拉姆斯和貝多芬面對後現代美學,該作品基於易於識別的主題結構和顯然再次成為傳統的寫作安排。這一系列作品構成了向新風格的過渡,李格悌在完全不同的層面上重新連接了他第一時期的某些元素,重現了巴托克的面貌。利蓋蒂的一大優點是擺脫了他自己風格的學院主義,包括他的歌劇特有的嘲笑,並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詮釋了後者的複合美學。
如果說第二時期的作品將其過程隱藏在旋律節奏的糾纏中,那麼第三時期的作品則充分展現了其深層結構。在那裡,我們發現了動機或主題實體,根據由幾個疊加層組成的書寫原理,以廣義多形法進行處理。鋼琴協奏曲(1984-1988)就是這種寫作的一個重要例子。從第一樂章開始,鋼琴呈現兩個獨立的節奏層,管弦樂團的韻律層將被加入其中。這些轉變會造成內在緊張,導致病情惡化,我們會因破裂而從一種傾向轉向另一種傾向。在後來的利蓋蒂那裡,形式通常被認為是一系列導致轉折點的過程,之後一個新的過程以不同的音色排列發展起來。在協奏曲的第四樂章中,李格悌從數學家伯努瓦·曼德爾布羅特揭示的分形中汲取靈感,開發了一種適用於局部結構和全局結構的形式。因此,我們可以注意到他對音樂形式的幾何或數學結構的應用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從他一開始對黃金分割的熱情,到埃爾諾·倫德瓦伊對巴托克音樂的分析,一直到分形形式,包括幻覺主義結構莫里茲·埃舍爾(Maurits Escher)的作品,他嘗試了某些轉換。但同時,利蓋蒂發展了深厚的旋律脈絡,尤其是在《小提琴協奏曲》(1990-1992)和《中提琴獨奏奏鳴曲》(1991-1994)中,這兩部作品充滿了特殊的情感,其中的樂句具有不尋常的抒情性。我們是否應該認為小提琴以及衍生出來的中提琴喚起了人們對童年的記憶,特別是那些在集中營中失蹤的弟弟的記憶?中提琴獨奏奏鳴曲以憂鬱的特蘭西瓦尼亞流行音樂開場。
因此,在20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的李格悌綜合中,我們發現了與民間傳說的聯繫,但擴展到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音樂,發展全音階旋律-和聲寫作的願望,既遠離音調恢復,也遠離廣義色差,並包括自然音程(他在圓號寫作或透過不同的弦樂斯科達拉中特別發展),對位法(旋律和節奏)的概括,作為音樂話語和作曲紋理的組織形式,以及本質上是脈動音樂,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基於不同的脈動電流,在第二階段被部分放棄。精湛技藝,既是一種表達形式,也是一種將材料推向極限的方式,是最新作品的核心,特別是《鋼琴研究》三本書(1985-2001)以及鋼琴和小提琴協奏曲。在所有這些作品中,表現力往往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推動力,伴隨著哀悼的形式,至少在表面上,這些哀悼的語氣透露出一種更主觀的語氣。第二個時期的尖銳諷刺在戲劇作品中達到了頂峰,但變得越來越罕見,儘管如此,在最後一部作品《Síppal, dobbal, nádihegedüvel》(2000)中重新出現,為聲樂和四位打擊樂手而創作,李格悌在其中找到了韋爾斯。
鋼琴研究構成了貫穿作曲家整個最後時期的共同線索:它們提供了里格的想像力、他的技術、美學和表現關注點的廣闊形象;它們是他音樂思想的真正實驗室。作曲家本人注意到了他的發明的觸覺維度,銘刻在作曲家鋼琴家(斯卡拉蒂、蕭邦、舒曼和德布西)的豐富譜系中,他希望屬於這些譜系。它受到不同非洲音樂的影響,也受到南對自動演奏鋼琴的影響,甚至是塞隆尼厄斯·蒙克的鋼琴的影響,這使得利蓋蒂找到了擺脫小節線的移動結構,並創造了由複雜的組合、從模式產生的現象。 《Désordre》是該系列共十五首作品的首部作品,它代表了利蓋蒂孜孜不倦追求的理念:從嚴格的秩序中營造出一種混亂的印象,並通過跨越不同的閾值引導聽者從簡單的想法走向複雜的配置。第二本書的最後一個研究《Coloana infinitä》受到布朗庫西同名雕塑的啟發,也揭示了一種不可阻擋且虛幻的進程,其中時間被視為空間;它突然停止,在鍵盤的最高高音處,以盡可能強烈的細微差別,彷彿被吸入真空。如果利蓋蒂的作品創造了一個充滿聲學和時空幻覺的想像世界,那麼它們也開啟了一個超越樂器和寫作組合可能性的想像空間。這是一種超越世俗的形式。為了思考無限的可能世界,我們必須達到極限位置。但同一項研究,如果以一種更擬人化的方式來理解,它類似於一種反抗的姿態,一種被推到力量極限的吶喊,一種超越現有極限的強烈願望。
李格悌的音樂探索了可以自發掌握的音樂表面(它包含事件、地標、基本形式)和複雜的結構之間的關係,這些複雜的結構通常基於無法立即掌握的規範過程。深層本身來自於事先的計算和緊密的組合,來自於作曲家強加給自己的法則,但大多數時候是在作曲時挪用、偏離的,以獲得想要的結果。因此,我們應該始終在某些紋理表面上平滑的連續性背後感知到最終會導致形式突變的微觀關節,或者在起伏不定的風格背後,感知到統一矛盾時刻的潛在連續性。這種幻覺主義的目標是一種頓悟,即每一個時刻的頓悟,即大恐怖結束的“此時此地”,也是整個作品的頓悟。同樣,建構與主體性之間的關係,包括戲劇性的時刻和他們自己的嘲笑,導致以矛盾的形式表達真理,超越傳統的二分法:它存在於它的運動本身中,但一種似乎被凍結的運動,並在不可簡化為統一的地層形式。如果利傑特的追求不是要達到思想的極限,以音樂的敏感形式,讓我們超越任何言語概念化,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個悖論。作曲家以最高技術水平實現這一計劃的能力使他的作品整體上成為他那個世紀最傑出的作品之一,成為他那個時代文化的重要參考。

